本站不再支持您的浏览器,360、sogou等浏览器请切换到极速模式,或升级您的浏览器到 更高版本!以获得更好的观看效果。关闭

首页
当前位置: 首页» 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
11月16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家哲学与家伦理”系列学术讲座第九期——“亚里士多德的‘准政治的’家庭”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廖申白教授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田海平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斯一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李涛副教授担任与谈人。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共有200余人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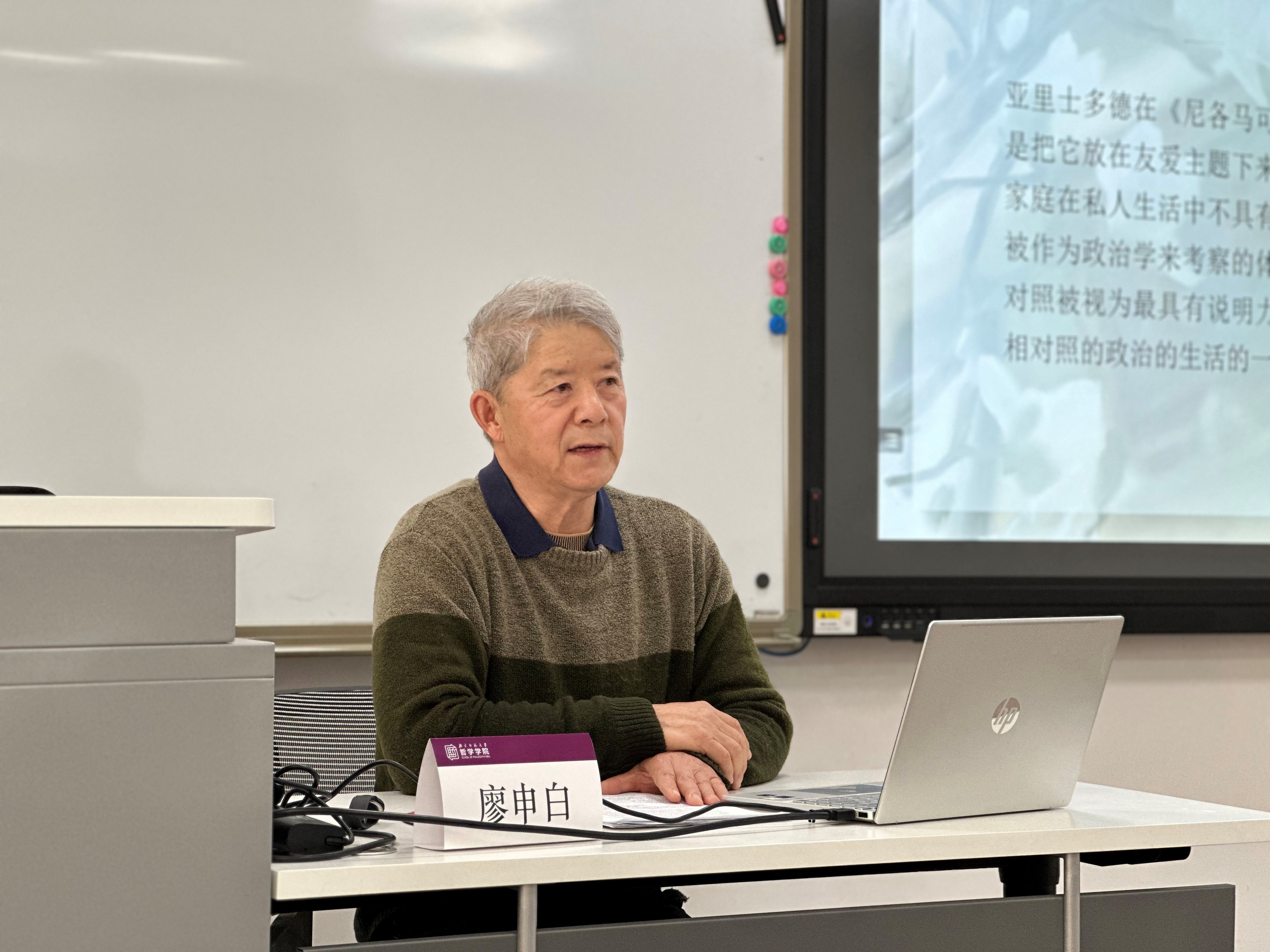
(主讲人:廖申白教授)
讲座伊始,廖申白教授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没有直接谈到家庭,因为伦理学在总体上被作为政治学来考察。把“家庭”置于“友爱”的主题下讨论,并不表明家庭在私人生活中不重要,而是表明在这一伦理学体系中,政治的生活与灵魂的活动之对照被视为最具有说服力的,“家庭的生活”则被作为“政治的生活”的附属例证来对待。由此,廖教授从努斯与“人”的生活的两重结构、家庭作为某种综合性“政体”、君主式父亲、妻子的地位与德性这四个部分着重阐述亚里士多德“准政治的”家庭。
在第一部分中,主要是关于努斯与“人”的生活的两重结构。廖申白教授提到,努斯是灵魂中最好的部分,它是灵魂的思考或沉思真实的能力,被誉为灵魂马车的“御手”、人的“实践性生命”之舟的“舵手”。所以,努斯应当是灵魂中最主宰的部分。治理者因为努斯才有好的秩序、好的生活。从灵魂论中引出的治理可以归纳为两种最重要的形式:一种是专制式的治理,另一种是共和式的治理。其中,灵魂之于肉体,是专制式的治理;灵魂内部(一个部分对其他部分,或者对其他那些部分),是共和式的治理。廖申白教授进一步解释道,灵魂的努斯对于欲望、激情或者情感的治理是共和式的治理,只有这样的治理才是最好的治理。也就是说,这样的治理,灵魂才是有秩序的,才能健康地发展,生命才能达到繁荣的状态。接着,廖申白教授谈到,努斯对灵魂的治理有两层实现:第一层是沉思(或者思考),也可以称之为沉思的生活或者哲学的生活。在第一层这里,思考是思想的运动,是思想与可思想的事物之间的际会。主动的努斯在思考、沉思的活动中指向可思考的对象,使它在思考的活动中显现出来,显现出它的真相。这是思想实现的方式。第二层是明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在活动中的实现。努斯在主导灵魂的非逻各斯部分的方式上:一是确定它们的好的活动方式,并发出命令;二是与它们一道在这样的活动中实现自身,成为实践性的理智德性。这意味着,感觉能力与行动能力能够按照正确的逻各斯,通过养成好的实践习惯成为伦理的德性。努斯主导灵魂的感觉能力与行动能力在实践性的生命活动中的实现,以及努斯自身即它的理论地沉思的部分,基于这样的实现,具现于人的两个基本层次的生活之中:第一个基本层次,自然是唯一原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由于繁育后代的自然需要而结合在一起,相互帮助地共同生活。这个结合体也自然地需要一个奴隶来提供日常生活必需资料的劳作。男人、女人和奴隶因此是最初的自然的家庭的三个要素。第二个基本层次,在自然的原因之上,加入了“共同生活”这个新的原因。“共同生活”在这里不再是指夫妇和他们作为主人与奴隶的自然的共同生活,而是指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与邻里和城邦其他公民的共同生活。这种生活被称为“政治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个人作为公民的生活。
接着廖教授进一步指出,政治的生活是最初的自然的家庭生活的生长和扩展,但已经不是最初的自然的家庭生活。首先,公民间的契约性的交易,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公民的友爱”,成为这种生活的基本纽带。其次,城邦因之需要有效的治理以保障这种契约的交往与正义相契合,需要以法律来划定正义与不正义的界限,并矫正已经产生的不正义。其三,公共生活成为城邦最重要的生活领域,成为公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其四,科学、艺术、哲学在公共生活领域繁荣发展,人类理智能力被激发,被运用和提升。因此,政治的生活成为私人生活的主要塑造者,同时,政治的生活目的就是培养能参与政治的生活的公民。
在第二部分中,廖申白教授围绕家庭作为某种综合性“政体”而展开。廖申白教授首先谈到,“家庭的生活”属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范畴,会受到政治生活强有力的塑造。其中,政治的生活的塑造不仅使得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具有了准政治性的关系的性质,也使得主人与家奴的关系具有了要依照城邦政治的生活来说明的非政治性关系的性质。由此,亚里士多德在家庭中看到了与政体相似的形式,如父子关系是君主制的形式,夫妻关系是贵族制的形式。同时,也可以看到它们的蜕变的形式,如坏的父子关系是僭主式的;坏的夫妻关系是寡头制的。在这里,僭主式的关系是非政治的主奴关系的正确的形式,因为在这种关系中获得的是主人的利益,而不是被统治的奴隶的利益。由此,廖教授提出,既然配偶关系是家庭的最初因,为何不能成为最重要的关系?他解释道,因为夫妻关系的最初因是繁育后代这一自然目的,它不能成为规定朝向培养一个公民子女的家庭生活的原因。而培养子女成为公民的目的要诉诸城邦政治的生活来说明。因此,君主制式、贵族制式的类比也就表明,在城邦政治之下的家庭中,夫妇的关系是从属于父子关系的。此外,在自然的家庭生活中的家主与作为“非家庭成员”的奴隶的关系,以“僭主制”的方式来处理的。
基于以上说明,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城邦政治生活的强有力的塑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考察下的“准政治的”公民家庭内部呈现出三重结构的“综合性政体”特质,即在父子关系上是君主制,父亲关心子女,为子女立法,并悉心培养他们成为公民;在夫妻关系上是贵族制,丈夫负责维系家庭的经济存在和子女的教养,妻子负责子女的哺育、日常照料和家庭日常事务的管理;在主奴关系上是僭主制,父亲或丈夫作为家主则应当以家庭生活的目的,令奴隶为主人的目的服务。男性公民在这个“综合性政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一身三任——他是一个君主式父亲,一个执政者丈夫,也是一位僭主式主人。
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君主式父亲。廖申白教授首先解释了君主式父亲的两层含义:其一是像君主适合做城邦的领导者一样,一个公民父亲适合做家庭的领导者;其二是像君主无求于自己的利益而操心其臣民的利益一样,在家庭中父亲无求于自己的利益而关心子女的利益。第一点使得父亲在家庭里的权威至高无上。第二点使得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与“神”同等重要,或类比于施惠者和受惠者。为承担起这种对于子女的政治的责任,父亲首先要关心子女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自身就美善的事物感受到快乐、喜欢,防止感受以非自然的方式变得过度或不及,对自然的欲望以合乎自然的方式去满足,尤其要防止欲望伴随变得过度或不及的感受朝非法方向野蛮生长成为习惯。同时,父亲作为家庭的主人、家庭资源的支配者,无求于自己的利益。家庭中的一切其他友爱——夫妇的、子女间的友爱——都是从这种君主式父亲对子女的友爱中派生出来的。
第四部分重点讲述了妻子的地位与德性。第二部分已经谈及夫妇的关系从属于父子关系,廖教授在第四部分对在城邦政治之下的家庭中,夫妇的关系从属于父子关系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的剖析。首先,廖教授以亚里士多德的论据为出发点进行分析,谈到了男女在自然禀赋上不平等,认为男子在体力与理智能力上高于女性。如男子强健、女性柔弱。同时,在理智能力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如男子在谋划、安排、考虑方面优越于女性,女性则专注于当下,缺少预见。基于这一区别,他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妇女不适合担任政治的治理与家庭的治理之责,因为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之目的的实现都需要明智地思考与运筹。丈夫应当是家庭中的治理者,妻子应该接受丈夫的治理。
与此同时,廖教授还从男主外、女主内的不同分工中引出夫妻双方在家庭作用中的不同等,如男性更擅长以明智地考虑来筹划和安排家庭经济,并在城邦公民生活中为家庭赢得荣誉与尊敬;女性则更擅长操持家庭日常生活,从属于丈夫,做丈夫的助手。同时廖申白教授补充道,丈夫和妻子更像是相互补充各自的缺欠的生活伴侣,以培养子女成为体面的公民,使家庭的荣誉得以继承为共同的目的。由此,通过对比亚里士多德关于妻子特具的德性不同于丈夫的德性——明智、节制、勇敢和正义,而是只具有部分德性,如节制和勇敢的德性。因此,回到家庭的生活范围内,妻子在较低程度上具有被看作属于一个好人的那些德性。所以,娴静是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的总德。对此,廖教授表示,这种观点放在当今社会会遭到部分人的反感,之所以没有避讳地将这一观点陈述出来,主要是因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虽不完全赞同,但值得大家讨论。
最后廖教授总结道,在城邦的“共同的生活”中,政治的生活,其塑造使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具有了“准政治的”关系的性质,也使主人与家奴的关系具有了要依照城邦政治的生活来说明的非政治性关系的性质。其中,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家庭生活的目的是培养男性子女成为体面、积极的城邦公民,培养女性子女胜任其未来的公民家庭生活。男性公民对于子女是“君主式父亲”。他无求于自己的利益而关心子女的利益。他的言语就是“逻各斯”,不是给他们的道德示范,而是向他们发布的命令。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是第二位的:妻子是家庭中被治理而不适合去治理家庭的成员。男性公民对于妻子是“贵族制”式的“执政者丈夫”。但无论在城邦生活中抑或家庭生活中,妻子都不具有治理者的德性,她分有人人可分有的伦理德性也在程度上逊色于丈夫。但是自由公民妻子在德性上仍高于非自由人公民。丈夫和妻子能够在共同培育子女的共同生活变得相互欣赏德性,形成“贵族式”友爱。但如果丈夫主宰包办一切,或妻子以继承人的权力治理家庭,公民家庭就蜕变为“寡头制”的。
听完廖申白教授的讲座,线上线下反响热烈。与谈阶段,陈斯一副教授、李涛副教授分别与廖申白教授进行了交流。

(与谈人:陈斯一教授)
陈斯一副教授表示,廖申白教授逻辑论证非常清晰,主要从亚里士多德整体的学术体系出发,一步步地切入到家庭的问题,再以家庭为线索,带出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学说、关于城邦政体的学说,最后回到家庭内部,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家庭关系、夫妇关系、妻子的位置等一系列非常细腻的学说。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他关于家庭的观念,可以被视作古希腊哲学比较典型的一套学说。如果放在古代哲学这个范畴之内,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还是比较重视家庭的,正如廖申白教授所阐释的,他仍然是从城邦政治的整体框架入手,去理解家庭的位置。因此家庭不可避免被政治化了,成为一个“准政治的”事情。家庭实际上是要为政治生活服务,所以亚里士多德将父子关系类比于君主制、将夫妇关系类比于贵族制,类似于我国家国同构的思想。只是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是从政治出发来理解家庭;中国思想则更多地是从家庭出发去理解政治。所以亚里士多德会以充分政治化的语言来讨论家庭里面的各种关系。
接着陈斯一副教授提出,他更愿意采取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待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主奴关系”。他认为奴隶不属于家庭。但是亚里士多德把奴隶放在家庭里面,实际是遮掩了这层关系所包含的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根底。当然,亚里士多德从规范性的意义上,提到主人是理性充分的,而奴隶是理性不充分的,甚至是没有理性的。诚如廖教授在讲座中也提到,这个说法没有太多的说服力。尤其是如果认为在自然的意义上,有些人天生就缺乏理性,所以就理当独立,那么显然是没有太多的说服力。陈教授进一步补充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之中将主流关系延伸到他对种族的理解上,从城邦视角出发去理解家庭,有两处值得我们批评讨论:其一:往家庭里面塞入一个僭主式关系,这其实是不太自然的关系,但亚里士多德把它论证成自然。其二:是延伸出来的,接近种族主义的偏见思想。当我们说古代文明会以自我为中心主义,华夏文明也是一样,但也似乎没亚里士多德的这么极端。
此外,陈斯一副教授还与廖申白老师分享了不同的观点:廖教授将父子关系解释为某种意义上的君臣关系,父亲是君主般的父亲。同时,廖教授关于施惠者和受惠者的解释里面也包含了高度的形而上学的维度,他认为这层解释更重要。父母爱孩子根源,都要在于父母爱自身,爱自身的存在!当然,这是一种诚实的学说,并不意味着它是在挖掘人性的自私等等,它只是诚实地去叙述他背后的形而上学的机理。随后,陈教授还提到,亚里士多德说的这套学说再叠加上他的性别主义偏见,会造成严重的困难。即通过形式、质料两分的方式来理解性别、生殖与生育,并倾向于把重心放在父亲身上,使得男女有别,男性和女性之间秩序分明、优劣有别,产生“心理性别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不对称性”,所以也使得亚里士多德很难解释母爱。
最后,陈斯一副教授还提到,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是完善的存在,女性是不完善的存在,不同于中国思想中的阴和阳,即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的关系。陈教授表示更赞成中国古代思想以一种相对圆融的方式去解释夫妇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等天人伦理伦常的视角,尽管在传统学说中,无论中西,大体上都是男权社会。他表示,希望通过中国思想在这一观点上的对待,来对比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并以此为补充。

(与谈人:李涛副教授)
李涛副教授将廖申白教授的讲座重点归纳为两点:其一,公民家庭内部呈现出一种“综合性政体”的特质;其二,家庭关系是“准政治的”,存在一种家和国之间的关系。对此从两个方面向廖申白教授提出请教:其一,是关于“主奴关系”该如何作进一步阐释。关于这一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面有很好的展现,即在家庭构成里面,有“管人学”,也有“管物学”。“管人学”可以划分为父亲学、丈夫学和主人学。“管物学”可以翻译成赚钱术、理财术等等。事实上,父亲学、丈夫学和主人学这三种关系都具有一定的张力,但把“物”(即赚钱术)也纳入其中,可能会破坏将整个家庭成员纳入政治学体系中的整体性。第二,基于廖教授主要谈及的家庭关系是“准政治”的这一问题。他提出如果纳入中西比较,西方很像是在用政治的关系去理解家庭,中国却更像是用家庭关系去理解政治。对此,他提到中国是不是要展示一种家国异构的设想,诚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的开篇中讲的三种统治关系:即政治统治(含君主统治)、家长统治、主人统治之间是一种并列式的关系,但它们各自有其要实现其目的,且差异性很大。至此,在李涛副教授看来这种统治关系存在一种异质性。尽管存在异质性,但亚里士多德经由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将家庭纳入城邦内部,其目的还是服务于政治学。这一点不同于中国传统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以孝治天下等原则。因此,他认为此处亚里士多德想突出家和国的异质性。
与此同时,李涛副教授还认为,除了先前提到最初的家国异构,到中间将家庭纳入到城邦,最后可能存在家庭原则异化政治原则。对此,他将这种异化原则分成了两种:其一,就是当父亲变坏了,家长统治就会从本质上关注被统治者的利益,变成只在乎统治者自己的利益。这属于坏的家庭原则对城邦政治的异化或者瓦解,即僭主制。其二,是慈父式的家长。慈父式的家长如果扩张到城邦里面,就会变“绝对君王制”。那么在绝对君王制的语境下,君王拥有最完善的美德,其他公民也都不需要发挥统治作用了,公民退化为小孩。这种绝对君王制,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也遭到了批评,即虽然绝对君王制很好,但如果在城邦政治里面实行家长统治,也将使得政治统治和家长统治无法区分了。
廖申白教授感谢了两位与谈人的精彩分享,并做出如下回应: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部分,把城邦之下的家庭生活放置在政治学里面,并认为政治学在城邦的一切事务上都是发布命令。由此,亚里士多德关于家庭的目的是由更好、更优越的生活,这也与其实践性的直接目的联系在一起。家庭的目的之于城邦而言,是使公民成为积极、体面的公民。然而,这一目的在自然的家庭生活里不仅没有,也不会产生;但在城邦产生了,就很重要。因此,廖申白教授认为亚里士多德旨在借助城邦的政治来说明家庭。
首先,关于亚里士多德是否是从城邦政治推到家庭生活,廖教授回应道,如果是从家庭生活的“准政治性”的解说来看,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否会上升至用政治来解释人类家庭,暂时没有推进至这一普遍性的论断。同时,关于中西比较而言,亚里士多德关于在希腊城邦生活中,对家庭生活的政治化这一点上,亚洲文化里面确实是没有的。事实上,中国所谓的“家国同构”,本质上是从天、地、人相合一的通融本源上发展出来的,而不是从城邦政治这里引过来。并且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而不是变异)的基础还有更深层次的根源,但绝不是城邦的政治社会。此外,廖教授也充分肯定了陈斯一副教授谈到的在施惠者和受惠者这一类比关系要上升至形而上学的维度,并认为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看到关于一个人的是或者存在。尽管对父爱的“爱”的这一本原里,涉及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但这个涉及却比较小。
接下来,关于家国同构和家国异构的对比,廖教授回应道,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达成“家国同构”这一共识,暂时不能断定。但就区别而言,中国的家庭是私人的领域,是非政治的,而亚里士多德谈论的家庭则是“准政治的”。至于亚里士多德是否要表达家国异构、中国是否更倾向于家国同构,暂且先搁置,但关于“构”的解释,廖申白教授将其放在“治理”中,并作了进一步讨论,他认为,城邦的政治结构和家庭规模是不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将最好的治理和最好的秩序状态结合在一起。认为灵魂是这样、政治城邦生活是这样、家庭社会也是这样,据此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生活与家庭生活之间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如果将“构”指向制度性的结构,则可以称之为“异构”。
最后,关于共和式治理(提问者使用的是政治统治)、家长的治理(提问者使用的是家长统治)与主人的治理(提问者使用的是主人统治),是否存在不一致。廖教授回应道,共和式治理是亚里士多德谈到的最好的治理的一种形式。但是家长的治理、主人的治理,这两者的含义差别却很大。家长的治理,是对妻子、对子女,而不包括对奴隶。主人的治理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怎么样使用奴隶的治理,一种是和奴隶(作为有生命的工具)的僭主治理。但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中,还涉及了对奴隶的教育。奴隶若能理解契约,那么主人和奴隶也可能发展成人的关系。总之,主人的治理在原理上是一个僭主性的治理,不是共和治理。而家长治理它包含着两个方面,是两种共和式治理的一种融合,既有对妻子的贵族式的治理,又有对子女的君主制的治理。
最后廖申白教授也对线上听众的提问作了回应。

(主持人:田海平教授)
讲座最后,田海平教授对整场讲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田海平教授指出,关于“准政治的”家庭等问题的思考对于我们进一步讨论家庭伦理问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案例,也让我们了解到生活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是如何看待家庭问题的。关于家庭伦理中情感与理性的讨论,中国关于“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观念属于情理逻辑,即以情在先,以理在后;而亚里士多德“准政治的”家庭,则更倾向理性。当今时代女性地位不断上升,那么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和家庭关系的讨论,哪些值得继承、哪些需要批判,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同样,中国儒家文化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构建,与亚里士多德政治论中讨论的君主治理、家长治理等政体结构之间,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比较。田海平教授认为,此次讲座与此前唐文明教授、樊和平教授等关于中国家庭伦理的阐述,形成了前后呼应,极大地丰富了家伦理系列的内容。

讲座结束后现场同学表达了对廖教授的崇敬与喜爱,纷纷拿出自己学习和珍藏的译著书籍请廖申白教授签名。廖老师一一询问同学们的名字签字留念,并与同学们亲切交流。
供稿:赵曼
供图:葛中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20 . All Rights Reserved






 电话:010-58802001
电话:010-58802001 传真:010-58802001
传真:010-58802001  E-mail:philoffice@bnu.edu.cn
E-mail:philoffice@bnu.edu.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外大街19号北师大前主楼8层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外大街19号北师大前主楼8层

